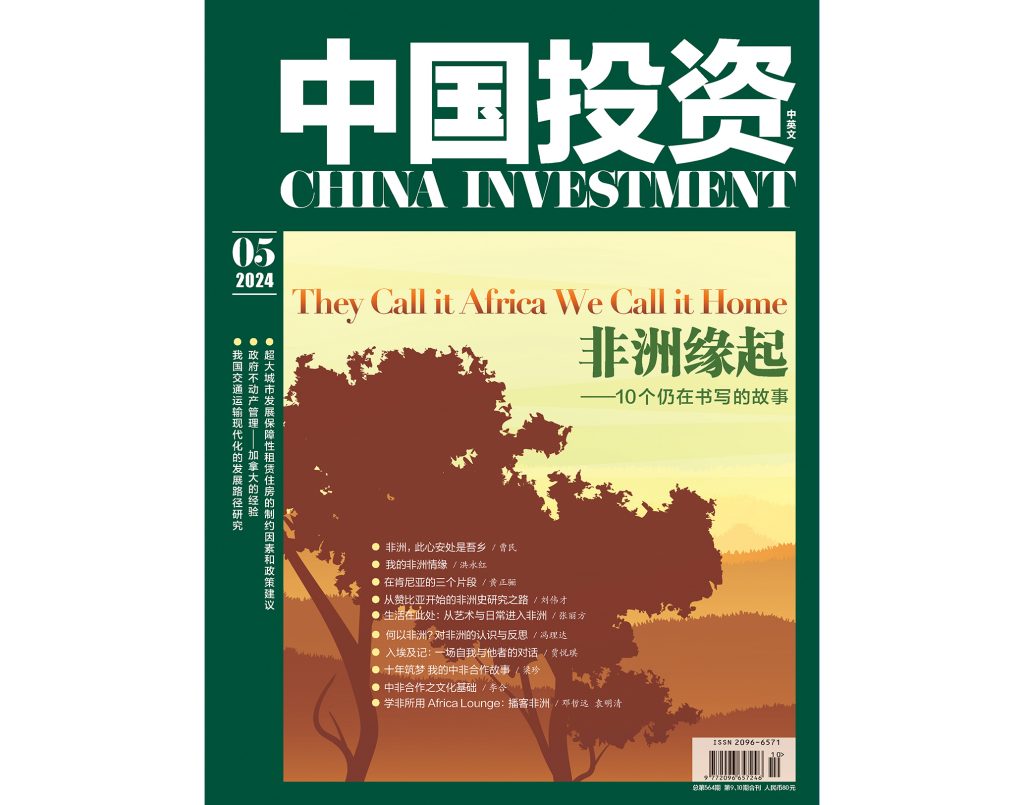
5月号封面故事
非洲缘起
——10个仍在书写的故事
● 我的非洲情缘 /洪永红
● 在肯尼亚的三个片段 / 刘伟才
● 生活在此处:从艺术与日常进入非洲 / 张丽方
● 何以非洲?对非洲的认识与反思 / 冯理达
● 入埃及记:一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 贾悦琪
● 十年筑梦 我的中非合作故事 / 梁珍
● 中非合作之文化基础 / 李合
● 学非所用Africa Lounge:播客非洲 / 邓哲远 袁明清

文|冯理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图片提供|冯理达
导读
●何以非洲?多元文明,城市病和难民
●何以非洲?大工地,国道局、马赛马拉的水塘
● 何以非洲?酋长、农民,大地上受苦的人
●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非洲人民

⬆ 作者(左一)与加纳波诺地区某村庄中土地被商业种植园征收的农民一家
如果有人问,对非洲有何印象,我脑海里仍首先闪现这样一幅场景:潮湿的热带海风,远方泛红的夕阳,摇曳的椰子树,奔跑的孩子,以及在马路中穿行、将商品稳稳地顶在头上的小商贩。这个带着明显刻板印象的画面,来自我2016年10月第一次踏上非洲国家——坦桑尼亚时,走出尼雷尔机场对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的第一瞥。那时正在读研究生二年级。在坦桑尼亚生活了近一年,之后硕士毕业读博,期间又相继在肯尼亚、加纳生活了一阵子。现在看起来,这幅画面只不过是非洲这个万花筒世界中的一片花色。于我而言,参与非洲研究、在非洲学习、生活的过程,既是认识非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不断审视自我,破除偏见的过程。

⬆ 达累斯萨拉姆街景
何以非洲?多元文明,城市病和难民
第一次去非洲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市度过,城市既是栖身之所,也是第一观察对象。不同于民族主义视角下,人们对单一民族或文化叙事的迷恋,东至桑给巴尔岛(Zanzibar),北至巴加莫约(Bagamoyo), 南至马菲亚(Mafia)、基尔瓦(Kilwa)等城市,构成了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欧洲文化、印度文化,甚至中国文化,同非洲本土文化交汇的斯瓦希里文明核心地带;从达市向内陆延伸,一批批非洲商人、以利文斯通(D. Livingstone)、提普·提卜(Tippu Tip)等为代表的探险家、传教士、奴隶贩子,以及后来的德、英殖民者和来自印度、中国的铁路工人,又将印度洋的海风带至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沿岸乌吉吉(Ujiji)、基戈马(Kigoma)等城镇。达累斯萨拉姆沟通了印度洋和非洲大湖区,链接了两地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坦桑尼亚的非洲文化本身,便是文明交融、碰撞、互鉴的产物。
在达市也感受到了一种割裂感:与多元文明共存的是悬殊的贫富差距及其带来的城市病。沿海地区的高楼耸立,但基农多尼区(Kinondoni)贫民窟内,斑驳的铁皮房、来自农村的移民,又构成了另一个世界;达市市区有着平坦的高速路、便捷的BRT公交,但在城市主干道的转角,却变成了凹凸不平的泥土路,阵雨过后,泥泞不堪;高档跑车和排着黑色尾气的日本二手公交行驶在同一条马路上,售票员挤出半个身位,边发出“嘬嘬”的声音,边拍打着车身揽客;在姆萨萨尼半岛(Msasani Peninsular)有许多家高档酒店,人们衣冠楚楚,而在城区的绿化带上,却也有成群的无家可归者——这一切也构成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的共同图景。与20世纪初期,卢加德(F. Lugard)、卡梅伦(D. Cameron)等来自大英帝国的非洲总督们所预想的并不一样,非洲国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共存、冲突、跃升、竞争,无时不在证明着非洲社会的动态感,以及不同地区、族裔之间的紧密联系,而曾经根深蒂固于西方人偏见中的“部落(tribe)”社会,或鸡犬相闻的田园风情,或许只存在于早期西方人类学家的著述中,和好莱坞的剧本里。
坦桑尼亚也存在着鲜为市民、游客所知晓的另一面: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在大湖区——卢旺达、布隆迪、刚果(金)的种族冲突中产生的数百万难民,相当一部分流落在了坦桑尼亚西部的难民营。到了2017年,随着对城市风光感到厌倦,我于是便坐上了前往坦-刚边境的长途大巴,前往边境地区的难民营。“难民”形象最能代表人们对非洲的偏见,但却又是切实存在、绕不开的话题。从尼雷尔(J. Nyerere)时代至今,虽然坦桑尼亚的难民政策屡有变化,但终归还是大湖区难民最好的避难所。在位于马卡雷(Makere)的涅鲁古素(Nyarugusu)难民营,我见到了规划整齐的安置房和卫生间、烤玉米和木薯的小摊,甚至Vodafone、Airtel、MTN的营业点和小学,也有被难民砍伐一空的灌木、持枪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以及拥堵在联合国难民署门前等待消息的人群,我坐在私人营运的黑摩托上,这些画面、声音、气味从身边闪过,杂糅在一起,构成了我第一次非洲行的另一面记忆。

⬆ 坦桑尼亚奔巴岛上中国安保公司雇员

⬆ 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博物馆
何以非洲?大工地,国道局、马赛马拉的水塘
第二次去非洲,前往肯尼亚,让我对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更清晰的认识。2019年初夏,我来到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一家国企实习。从内罗毕机场到中企项目部的路上,感觉这个内陆高原城市好似一个巨大的项目工地,到处都是热火朝天的景象。我实习的中企承包了从内罗毕到某地的公路项目。该路段全程20多公里,也是肯尼亚通往乌干达、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等国的交通大动脉。在来到工地之前,以为工程项目只需要按部就班施工就好,但与想象的不同,项目还需要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关系。该项目横跨了多个郡、选区和十余个社区,社会环境复杂。
印象较深的有两件事,第一是项目部和肯尼亚国道局等政府部门间的纠葛。路政项目每天有许多大渣土车,在不远处东非大裂谷下的石料场和内罗毕郊区的施工路段之间,往返运送铣刨料、土方和沥青等,但吊诡的是,肯尼亚国道局却常常跑到施工路段抓车辆超重,一个月内竟有8辆大车因所谓的超载被抓,动辄几十万肯先令的罚款,并扣押车辆。据了解,施工单位和业主单位虽然早已就该问题达成谅解协议,但国道局对项目运输车辆紧盯不放的原因在于,一段时间内肯尼亚全国上下开展了“整治超载”的运动,国道局作为官僚系统的一员,自然要响应号召;另外,国道局虽然作为业主单位,但“地主家也没余粮”,若要维护道路、维持机构的运营,便需要更多的资金。因而趁着“整治超载”的契机,国道局将项目的运输车辆视作摇钱树,不断对项目车辆进行突击检查。项目部一方面面临着因赎回被扣车辆带来的巨额保释金,另一方面还需要应对国道局因项目部拒绝缴纳罚款而提起的诉讼。在项目部期间,我也好几次跟着负责人大哥去找相关部门的领导,或跑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应对办法,也曾在法院排队,听着晦涩的法律词汇、昏昏欲睡地等候庭审。直到结束实习临走时,有的渣土车还在国道局扣押着。
同国道局的交涉只是项目部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项目部负责人还是当地警察局、法院、世界银行、国会等官僚系统的常客,有时还会因扬尘、噪音、私人土地租赁等问题,被周边老百姓投诉,不得不每天奔走,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第二是中企在马赛马拉修建的道路以及大型水塘。在内罗毕待了一阵子后,我又来到了位于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另一个道路项目部。谈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无数中国人会想起广袤的大草原、花豹、狮子、动物大迁徙,以及赵忠祥老师浑厚的声音,但是鲜为人知的是,从内罗毕到马赛马拉的路,也是由中国企业修建的。在修路之前,去往马赛马拉只有夯土路,道路条件十分恶劣。但是中国工程队到来后,用厚厚的沥青马路,将马赛马拉链接到了肯尼亚全国的道路交通网内,使当地的区位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中企在修建道路之余,还为当地的马赛人建起了一百多个水塘,解决了马赛人和牲畜的饮水问题。据项目部负责人介绍,在施工初期,工程队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克服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是如何处理好同当地马赛人社区之间的关系,当发现旱季饮水问题困扰马赛人世世代代生存时,帮助马赛社区修建水塘,成为沟通马赛人和中国工程队感情的桥梁。
驱车行驶在平稳的柏油马路上,路边是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草原上的水塘在阳光下波光粼粼,周边聚集起了取水的居民和他们牵来的牛羊,我也成了中国在肯尼亚项目成果的受益人,免受颠簸之苦。中国企业在肯尼亚的项目众多,例如著名的蒙内铁路。一个个不同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和民生,还为非洲国家带去了发展的更多可能性。

⬆ 肯尼亚运水的农民

⬆ 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公园
何以非洲?酋长、农民,大地上受苦的人
第三次踏上非洲是在2021年,当时全球疫情严重,为了完成博士论文的调研和材料搜集,我来到了西非国家加纳,主要考察加纳的土地制度,在闲暇时,也对加纳首都阿克拉,周边城镇以及中北部个别省份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调研。不同于前两次,这次在非洲时间更长,也接触到了酋长、普通的农民,以及跨国公司在非洲的种植园项目。在加纳的两年,使我对非洲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认识,尤其是对非洲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产生了新的思考。
说起酋长,大多数中国人都将其视为非洲文化的代表,确实如此,但也并非事实的全貌。加纳的酋长相对于部分非洲国家而言,权力较大,依照习惯法控制着全国80%左右的土地,尤其是最高酋长(paramount chief或Omanhene),且这一权利也受到国家宪法的保护。当我们在某些语境下将“非洲酋长”形象娱乐化、猎奇化时,许多加纳农村地区的农民,一生都生活在酋长的影响之下,许多人甚至是酋长的终身佃户,通过世世代代向酋长缴纳实物地租,换取土地的使用权,而这一微薄的权利也并不稳固。
在加纳北部某省的一个村子,我接触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位以种植山芋为生的八旬老者,在20世纪60年代从加纳西北部移民至此,通过每年向当地酋长缴纳实物地租,获得土地的使用权。但近些年来,随着来自北方国家市场对热带水果的需求日盛,越来越多的土地被来自城市的商人和企业征用,种植腰果、芒果、菠萝等热带水果出口。这位老者的土地也不例外,在一年多以前,他耕作的土地被酋长转租给了一位来自城市的商人,农田也即将要转为芒果种植园。至于这位老者的土地使用权,由于和酋长之间是租佃关系,无法得到任何补偿。据老者说,收完这一季山芋,便要带着自己的孙子离开这个地方,另寻出路。
另一个案例位于邻近省份的小镇。一家欧洲生物能源企业在该地区向最高酋长租赁了上万公顷的农田,建造了一片作为生物质燃料的桉树种植园,这家企业土地租赁协议涉及邻近几个村落的耕地,但由于酋长在土地事务上权力的专断性,并没有将土地租赁协议同利益相关的村落进行协商,或赔偿失去土地村落的损失,以至于村民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被公司以各种方式圈占了起来,并被禁止入内。这个对外宣传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西方跨国公司,最终却以传统的方式,破坏了民众的生计。
在加纳,类似的例子屡见不鲜,甚至包括一直被某些媒体作为污名化中国工具的小规模非法采金(galamsey),土地的出让,很大程度上也是酋长、本地官僚等精英团体同跨国资本之间合谋的结果。以上例子并非要站在制高点去反对什么,只是希望说明一点:当前非洲存在的社会问题,确实来自非洲本身的制度性困境,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当不平等国际体系——包括劳动分工体系、剩余分配体系等——同非洲本土性问题相结合时,其破坏性或许是普通非洲人难以想象的。

⬆ 在肯尼亚的中企在施工过程中征询周边群众的意见

⬆ 加纳农民在展示山芋种植
结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非洲人民
达累斯萨拉姆仍在印度洋海风的吹拂下,通勤的市民不紧不慢地赶着公交,印度人社区贴好了毗湿奴的神像,远方又响起了可兰经的诵读声;肯尼亚中国工程队将高速路铺到了边境的村镇,马赛人掬起清泉,不再期盼雨季;加纳的农民站在农田边,看着硕果累累的可可、地上沉甸甸的山芋,欢喜于今年的收成……。回头看自己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大地之时,已是差不多十年前,我也在学习与研究中,不断破除偏见、重新认识非洲,但要回答“什么是非洲”,却越发显得困难,因为非洲足够广袤,足够多元,足够复杂。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非洲是一个既普通又特殊的地方。
它的普通之处在于,这里生活的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性格和脾气,这些特质从我们每日乘地铁、坐公交、买菜、上班时遇到的千千万万、形形色色的人身上都能找到相似之处,他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在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努力;非洲的社会和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有着和谐和宁静,也有着令人头疼的冲突与问题。如果将我们研究的对象,贴上特殊或固定的标签,那么他们便不再是和我们同等的人或社会,而是被凝视的客体。
特殊之处则在于,同中国相比,非洲受到国际体系影响更大。在非洲内陆的某位自耕农,远比中国种植水稻、小麦的农民,距离世界市场更近,受跨国行为者的影响更深。换句话说,在课本中出现的不平等国际体系是切实存在、不可忽视的,我们在关注非洲本国制度性问题时,国际与全球的视角应该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苍穹。因此,对非洲以及全球千千万万处于国际体系中的普通人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来自遥远东方国家的理论、政策,也是伟大的理想,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与生活方式。
自2023年年中从加纳回到中国以来,和其他应届毕业生一样,经历了求职、论文答辩、毕业、工作,到今天已经一年了。如今,非洲研究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未来,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我也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