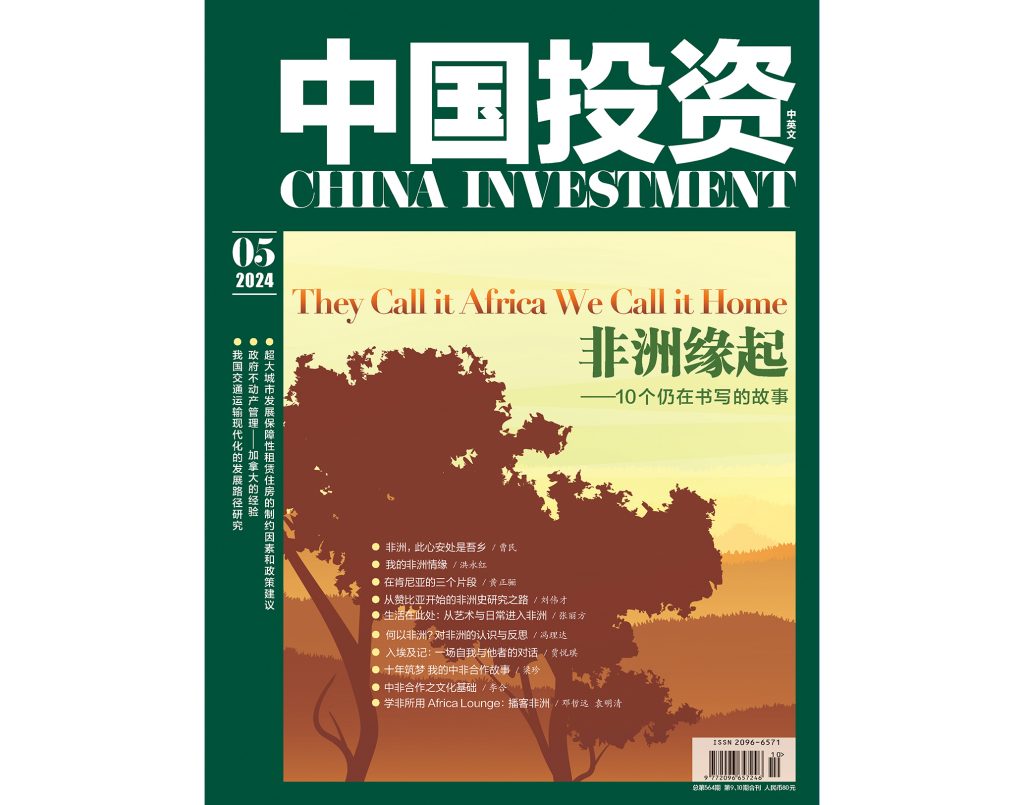
5月号封面故事
非洲缘起
——10个仍在书写的故事
● 我的非洲情缘 /洪永红
● 在肯尼亚的三个片段 / 刘伟才
● 生活在此处:从艺术与日常进入非洲 / 张丽方
● 何以非洲?对非洲的认识与反思 / 冯理达
● 入埃及记:一场自我与他者的对话 / 贾悦琪
● 十年筑梦 我的中非合作故事 / 梁珍
● 中非合作之文化基础 / 李合
● 学非所用Africa Lounge:播客非洲 / 邓哲远 袁明清

文|张丽方 南非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博士候选人 图片提供|张丽方
导读
●求学之路:从北京到马坎达小镇
●艺术作为认知与参与的路径
●生活在此处

⬆ 2014年作者在援埃塞小水电项目开工典礼
开始在脑海里构思这篇回顾的时候,我正在仓皇地收拾行李,准备再一次搬家。这倒不是计划的时间不充裕,而是因为在提交毕业论文之后,我开始隐隐感到要离开这片大陆的焦虑,于是更加投入地奔波于其他与告别无关的工作和琐事,在游离中耽搁到了租期截止的最后几天。我住在一座近百年历史的老公寓楼顶层,走出通往天台的小门,就可以饱览约翰内斯堡的城市景观:往北可以看到远处新兴的商业区和近处绿树掩映的住房,往南则可以看到常被作为约堡地标而同时又以危险昭著的老城里耸立的高楼。入秋之后,或深红或浅黄,这座城市再一次向我揭示它的不同面貌。冰雹、晚霞、暴雨,它所有不平庸的傍晚都在此刻重叠,预告着未来我对它们的怀念。
非洲于我而言已经过于具体,以至于我甚至很少在日常情景中提起“非洲”这个词本身。事实上,我尚未踏足这片大陆的绝大部分国家,但那些生活或调研过的地方却又不足以概括此时言说的对象。我如此明确地不愿远离的“非洲”究竟是什么?吸引我在短暂告别之前就开始想象重逢的又是什么?从2018年2月到眼下的2024年4月,这六年多的每一处居所、每一条逗留过的街道、每一次容纳不同观点的讨论、每一个与我产生连接的人或每一幅打动我的艺术作品,都使我在外来观察者和内在体验者的张力中剧烈成长,并同时重塑着我对非洲的认知。

⬆ 非洲与南南艺术研究项目办公空间与展厅

⬆ 校园高处看午后的小镇

⬆ 从住处看到遥望约堡老城夜幕降临
求学之路:从北京到马坎达小镇
2018年农历正月初三,我在家人的担忧和祝福中拖着行李箱离开湿冷的南方小城,辗转三十个小时后在南非的海滨城市伊丽莎白港落地。眼前一览无余的停机坪、行李提取处和机场出口之间只隔着两扇玻璃门,其规模和简陋程度让我想起国内小城市的汽车站。我到提前联系好的大巴车接待处获取信息后,加入了机场外已经排起的长队。长途跋涉的疲劳和南半球盛夏热烈的阳光让人一时恍惚,我没有心思观察周围的人群或想象位于小镇马坎达的校园,只感到十分焦灼,等待如此漫长。把行李塞进姗姗来迟的大巴车的同时,我脑海中闪过疑问:我千里迢迢来这里做什么?直到大巴缓缓驶出伊丽莎白港,碧蓝的海岸、空旷的道路和开阔的视野在眼前展开,我突然觉得未来的某一天我必定会怀念这段前往未知的旅途,内心涌起了久违的表达的欲望,这让我感到无比喜悦。但彼时的我也未曾料想,我会在南非度过六年的硕士和博士求学生涯。
“为什么到非洲/南非上学?”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一个简短有效的回答是“因为我学习非洲艺术”。有些人心领神会地点点头,有些人则会继续追问,“但是为什么?你怎么到这儿的?”。我本科就读的院系是经济管理,数据、税法和财会知识对于我毫无吸引力。在逃课和考前通宵的日常里,我成为图书馆文学书架的常客,并最终选择研究生考试进入了非洲文学方向的学习。彼时,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作品之外,我最早接触的小说《瓦解》和史诗《松迪亚塔》都是在北上的长途火车上阅读的,留下了一些关于“传统”、“信仰”和“英雄悲剧”等宏大而抽象的叙事碎片。入学之后,图书馆里寥寥的非洲文学译本、尼日利亚外教的文学课、非洲研究入门、非洲民族主义及非洲史等课程让我对这片大陆有了一些零星的认识,殖民与去殖民、种族主义与泛非主义以及语言、政治和女性等议题逐渐替代了草原、动物这些单一或刻板的印象。但那是由真实与虚构的人物、史实与传说以及错综复杂的争论所构成的话语层面的非洲,在地经验仍然离我十分遥远。
2016年2月我第一次到南非,为期一月的调研之旅事实上更接近文化观光,我和中文系的王丽学姐参观了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许多景点:博物馆、曼德拉广场、索韦托、好望角、长街等等;一位南非留学生的家人也带我们访问了开普敦的三个黑人城镇(township)。高速公路、商场和欧式建筑,甚或城市公园、海滩和温和的气候,都是彼时的我们不太熟悉的非洲。以往通过文本形成的想象并没有在眼前的现实中落地,而这次旅程留下的一些印象却从此影响着我的阅读,尤其是种族隔离历史遗留的城市空间结构:绿荫环绕、基础设施完善的住宅区和拥挤密集的黑人城镇泾渭分明。我回程的行李箱中塞满了毕业论文研究对象扎克斯·姆达(Zakes Mda)的小说,最终选择分析的文本也与南非的种族历史和空间结构息息相关。
这些经历让我意识到,继续学习非洲文化,浸润在它的语境中是十分重要的。毕业之际,我开始在网上寻找非洲不同国家高校的相关项目,并最终申请了南非罗德斯大学(Rhodes University)为期两年的艺术史硕士项目,成为我导师茹丝·辛巴奥教授(Ruth Simbao)所成立的“非洲与南南艺术”(Arts of Africa and Global Souths)研究项目的一员。南南艺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主要由研究员、行政人员以及包括我在内的研究生组成,除了团队成员们的办公空间外还有一个车库改造的展厅。我们在小镇举办的南非国家艺术节有固定参与项目,主要是一些艺术家对谈和展览;另外,导师每年也会邀请来自非洲大陆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学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驻地创作,并通常以一个展览结束。当然,疫情之后是另一番景象。
罗德斯大学这所百年老校的艺术系虽然历史悠久,但由于诸多原因,并没有关于非洲艺术的系统性课程。因而,我从对非洲当代艺术一无所知的状态直接进入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可以说,我所获得的大部分关于非洲艺术、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知识,都是受益于艺术家、周围的朋友、实践参与及一些切身经历。南南团队的包容和善意让我很快开始适应这个新环境,他们总是慷慨地分享关于生活和艺术的知识,不羞于表达自己与他人不同的观点,这也使我更加融入团队。在小镇的四年多里,我参与了大部份活动和展览的筹备,拍照、挂作品、钻钉子、刷墙甚至锯过木头,也主持过许多场艺术家对谈,不再怯于提问、讨论与争辩。艺术家们的工作室成为我真正的课堂,我有时会和他们聊作品,倾听他们分享如何选择材料与色彩,如何通过视觉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如何以创造性应对现实条件和限制;我们有时也会讨论社会议题和生活琐碎。这两年特殊而珍贵的学习经历不仅给我带来巨大的能量,也让我相信学术研究可以不枯燥,知识以及知识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并决定继续在南非读博。如今想来,也许正是好奇、对未知和可能性的向往以及拥抱惊喜和意外的勇气,让我感到自己和这片大陆产生了深刻的关联。而艺术不仅仅是我所学专业,也是我理解非洲的路径,它甚至构成这种关联本身。

⬆ 与团队一起为姆瓦巴布展

⬆ 塔卡迪瓦在津巴布韦国家艺术馆个展开幕
艺术作为认知与参与的路径
我是系里第一个中国学生,由于导师对中非关系十分感兴趣,于是在共同商议之后,我的硕士选题确定为非洲当代艺术对中非议题的呈现。非常幸运的是,来自赞比亚的艺术家斯塔利·姆瓦巴(Stary Mwaba)此时也在罗德斯大学,创作一组与中赞关系相关的作品。于是,我入学两周后就开始频繁地访问他的工作室。在我对中非关系相关讨论进行更广泛深入的了解之前,我是先从姆瓦巴的作品和故事进入这一话题。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家人与中国直接或间接的渊源,例如他住在坦赞铁路沿线的祖母以及在铜带省采矿并与中国商人交易的堂兄。姆瓦巴的作品把我带入中国援建的这个历史性工程和赞比亚的铜矿业,他讲述的故事及为创作而进行的调研准备也让我更加关注这个话题下的个体视角与叙事。
2018年6月,津巴布韦艺术家莫法特·塔卡迪瓦(Moffat Takadiwa)到小镇参与南非国家艺术节并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驻留。塔卡迪瓦大部分作品是以废弃物为原材料,其中就包括以中国进口小商品的消费剩余,如廉价香水的包装、电子产品垃圾等。于是,我又幸运地成为另一位研究对象工作室的常客,得以有机会时常和他讨论作品中关心的话题,并近距离地观察他的创作过程。同年11月,在开题通过后,我前往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进行我的第一次田野调研。在网络上搜索哈拉雷,最先看到的总是蓝花楹盛开、岁月静好的景象,但它又同时与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机能瘫痪和失业率极高绑定。我无法通过这些看似矛盾的词汇想象具体的画面,直到抵达熙熙攘攘、忙碌喧闹和充满能量的哈拉雷。我立刻理解塔卡迪瓦对艺术材料的选择,甚至觉得在他作品中看到了这个城市的节奏。我跟着塔卡迪瓦访问了他和许多青年艺术家位于社区公共活动中心的共享工作室,并一同前往他搜集材料的城郊垃圾场,认识了他的合作者:一个以拾荒为生的家庭。我开始意识到,工作室只容纳了他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他的艺术实践应该在更广义的社会城市空间中展开。
田野调研之后,我调整了论文写作方向,从艺术作品对中国形象和中非关系的呈现,转换为理解这些艺术家在谈及中国时他们究竟在讨论什么。例如,姆瓦巴关心的是坦赞铁路沿线普通人的生活和在危险的铜渣山体中挖矿的青年的个体经验;塔卡迪瓦想要探索和介入的是哈拉雷这个后殖民城市的生产消费文化和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与应对途径。在进行课题调研的同时,我也开始关注更多的非洲当代艺术家,如果一定要指出他们的作品有什么共同特征,其中一点就是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视觉语言和艺术创新可以忽略,而是在强调他们的作品与日常经验、政治历史和公共议题的密切关系,以及对我理解非洲社会的影响和启发。非洲当代艺术研究的本质是跨学科和跨地域的,我通过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切入不同议题,从赞比亚的铜矿业到哈拉雷的城市历史,从南部非洲种族隔离时期的啤酒垄断机制到女性在独立斗争叙事中的缺失,从艺术基础设施到某个具体图像的流动与变迁等等。在和一些艺术家长期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开始合作策划展览和工作坊等活动,这些实践参与也成为我在非洲生活的一部分。

⬆ 塔卡迪瓦在哈拉雷收集创作材料
生活在此处
在到达南非初期,我大抵持着一种留学生心态:关心的主要是校园和研究,尽管充满好奇也时时观察,但与周遭环境多少保持着某种程度的疏离。只有两条主街的小镇只是学校的所在地,其中发生的诸多事件,即使会影响到日常,却更多的是他人的生活。刻板印象并不是单向的,在与陌生人的相遇和交谈中,我时常碰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例如,你会不会功夫?你们中国人都吃狗肉/蛇肉/蝙蝠吗?甚至也有不好意思问出口的朋友,在我邀请他们到中国餐厅吃饭时面露难色,不断地确认盘子里的食材是什么肉。我在北京时,曾经热情地和一位利比里亚同学分享我的南非之旅;类似地,小镇的一位老太太在得知我来自中国后,仍然兴奋地给我描述她儿子的韩国女友。倘若保持开放和好奇,这些日常小插曲并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此自我调侃甚至可以破冰。
我是在疫情之后,产生强烈的“生活在此处”的意识。宣布为国家灾难状态的南非封锁十分严格,我作为唯一的中国人和20多位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研究生留守在空荡荡的校园里。在放弃了找机会回国“避难”的念头后,我内心甚至涌出一个悲壮的词——“共进退”:我要和小镇一同等待这场世纪大流行的结束,等待学校再次开放,艺术节重新回归。也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荒诞的时刻,宿舍楼里这些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成为互相给予关怀的集体,让常常独来独往的我也开始拥抱甚至热爱人群。在几位投票选出的舍管们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庆祝节日和每一位同学的生日,也一起组织游戏和打扫公共区域卫生;甚至在停水的日子里,轮流提着水桶互相帮助去打水。我在这些非洲同学面前自惭形秽,他们不仅是各自领域优秀的研究者,还具有极高的生活技能和心理调节能力,在危机之下同样能享受和创造生活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家务、烘焙不在话下,还能组织室外电影、主题派对和健身活动。彼时,在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歧视中国人甚至亚洲人的言论,但这些和我一样深处异国他乡的非洲同学却给予我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连接与善意。
2022年末,带着体验南非城市生活的想法,决定搬到约翰内斯堡,这个时常被“危险”叙事裹挟的地方。 “不安全”、“贫民窟”或者“脏乱差”是非洲众多城市的标签,和“原始”、“神秘”这些词一同把非洲妖魔化或浪漫化为整体,反而阻碍了人们去了解、发现和学习。约翰内斯堡尽管存在着治安、贫富差距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但它也是一座极其多元的现代大都市,迷人而不可定义。尽管只搬到这里一年半,我已经通过切身经验在脑海中绘制出一张自己的生活-文化地图:看艺术展览的路线、听音乐看演出的场所、视野好且安静的咖啡店或者吃南非菜、埃塞菜、墨西哥菜的首选餐厅,以及不同月份的电影节、音乐节和艺术博览会。然而,这座城市仍然在不断展开它的经纬,向我介绍尚未去过的地方,并在揭示自身历史和真实困境的同时,也重塑着我与它甚至与世界的关系。

⬆ 艺术家赛碧蒂
作为一个生活在此处的外来者,我想引用一段对话结束这篇以不同片刻勾勒的简要回述,并与所有直接或间接遇见过“非洲”的朋友共勉。今年五一劳动节之际,在约翰内斯堡大学的艺术馆中,策展人和艺术史学者格尼韦(Thembinkosi Goniwe)与艺术家赛碧蒂(Mmakgabo Helen Sebidi)就后者的个展进行对谈。观众提问环节,一位在城市长大的青年学生听了赛碧蒂讲述对乡村的回忆之后,十分谦逊地坦诚自己对农村及其文化重要性的无知,并提问道:
“您认为我们这些青年学者能为更好地呈现(represent)农村做什么?”。
81岁高龄的艺术家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的建议是,去农村去寻找帮助,告诉他们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处在深深的黑暗中……”。
格尼韦总结并补充道:
“我的理解是,直接地说,我们要停止居高临下甚至‘施恩’的心态。与其问我们能为他们做什么,不如直接去问问他们,因为他们生活在那里。受过教育的人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总在代表他人说话,我自己也不例外。我们创造术语、界定范畴,用话语、图像和各种形式去呈现他人,却不曾与他们进行过任何真正的对话。我们在安全的图书馆里阅读,我们撰写著作,成为教授,但我们却未曾体验过他们生活的气息。她(指赛碧蒂)是在呼吁我们到那儿去。因为身处黑暗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处在对他们的生活一无所知的黑暗之中。”

